男女主角分别是赵泗嬴政的现代都市小说《扶摇直上赵泗嬴政大结局》,由网络作家“徐福”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扶摇直上》是由作者“徐福”创作的火热小说。讲述了:穿越大秦,成为出海为始皇求长生药船队的一名船员......飘洋八年,终回故土,成为大秦第一位海归。嬴政:可有仙山?可有仙人?可有仙药?赵泗:无......始皇帝:无功而返,此乃死罪......赵泗:“臣有物要献!”说罢,赵泗摊开一块破布,掏出几袋子皱巴巴的种子。“陛下,此乃世界地图,大秦尚未四海归一,此乃红薯土豆,亩产千斤!此乃......
《扶摇直上赵泗嬴政大结局》精彩片段
而且这些履历都很好证实,船上四百多人,不可能串供一致,分开询问,很容易问出真假。
但是,始皇帝敏锐的捕捉到了一点。
赵泗的船队不是第一时间靠港,而是在一个月前滞留海外,单独派了一艘船和琅琊本地官府接触以后才集体靠港。
恰好当时始皇帝大巡天下,经过琅琊,得知出海寻仙的船队归来,于是特意前往琅琊等待,这才有了今日赵泗船队靠港,始皇帝亲至的场面。
赵泗沉默片刻开口说道:“所为归家罢了。”
实际上,不管是怎么样的信念,都没有思乡和归家来的强烈。
真正不顾一切都想要执行王命的是极少数,大多数跟随赵泗夺船出海的人,内心最深的执念还是归家。
执行王命,本质上是不愿流落海外的一种借口。
留下来很简单,但是留下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出去执行王命,就有那么一丝虚无缥缈的归家的希望。
哪怕很多人都知道,寻仙之事,十分飘渺,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王命,重新踏足故乡土地。
但是很多人,都情愿死在归家的路上。
“彼时出海,船上人手,又有哪个没有家眷?一应童男童女,有的还是家中独子。”赵泗开口说道。
这才是这个时代的沉重之处。
徐福出海是诸夏历史上第一次远洋探索和航行,听起来波澜壮阔,充满了史诗的味道。
然而本质上,这次出海是徐福一个人的骗局,和几千个家庭的悲剧。
工匠,农人,士卒,告别家中孩儿,最终沦落海外……终生不得归家。
三千童男童女,他们尚在懵懂之时,就在父母悲戚的哭声之中踏上海船,从此往后人生的几十年,再也见不到亲人的面目。
记忆会在她们脑海里逐渐模糊消散,乃至于只是记得自己是有父母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了。
历史华丽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眼泪书写而成。
而徐福出海,也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插曲罢了。
谁又不想回家?所有人都想回家。
他们在畏惧什么?还不是畏惧未能完成王命而被牵连诛杀?
这或许是徐福的欺骗,可是没人愿意用生命试探真假。
赵泗甚至无法揭开徐福的骗局,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徐福对峙,他不能代表始皇帝。
所有人都想归家,但只有九百多个和赵泗夺船出走,留在扶桑的本质上也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始皇帝看着赵泗,眼神凝重。
“你在怨朕?”
赵泗诚恳的摇了摇头。"
始皇帝本能的开始了思考。
作为横扫八荒六合的始皇帝,当得知世界广袤肥美,看到完整的世界地图的第一个瞬间,产生的想法是理所应当的据为己有。
就如同他初登王位的那一刻,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天下应该在自己手下混为一谈,天底下都应该只写一种文字说一种语言用同一种度量衡。
当然,他知道这样的想法是荒谬的。
始皇帝甚至可以想象的到,世界之极另一端的秦吏,光是得知中央政治变动,恐怕都得要十几年的时间,做出反应甚至需要几十年。
更不用提各地税收的征取。
始皇帝可以为了从匈奴人手中夺走河套之地修建一条秦直道以方便运输物资。
可是世界呢?
难道再修一条秦直道?
那要有多长多远,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作为一个勤政但并不是很爱民的皇帝,始皇帝对于大秦的财政情况以及承受能力有着清晰的认知。
可以这么说,目前的秦国,已经在极限负荷了。
河套地区三十万秦军,修建长城的数十万征夫。
百越地区的六十万秦军……
秦始皇陵,正在轰轰烈烈开工的阿房宫。
天底下驰道的继续铺设和修建。
始皇帝手下的秦国宛如一台精密的仪器,始皇帝则是最敏锐的操控者,让帝国的最大功率运转的情况下,铺设各式各样的大工程,同时又不会猝然崩塌。
赵泗是一个热爱冒险的疯子,不然上一辈子也接不到红牛赞助。
始皇帝骨子里也有疯狂的冒险因子。
他从来不会畏手畏脚,在缔造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以后,不顾一切的开启了帝制先河,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前无古人甚至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最起码在这个时代绝对足够离经叛道。
他做的每一个大工程都是在挑战大秦帝国的承受极限。
客观来说,始皇帝同时进行的大工程,单单拿出来一件都足够一个王朝无力分心。
偏偏始皇帝能一块来,还能够在极限情况下反复横跳。
他手下的秦国,永远在极限负荷下疯狂运转。
当然,更可怕的是,极限运转情况下的大秦,可能藏的还有后备隐藏能源。
但是始皇帝已经五十岁了,选不再是那个产生想法就不顾一切想要实现的年纪。
别说征服世界,大秦踏出四极恐怕都需要十年乃至于几十年的时间。
始皇帝收敛想法,又继续询问赵泗一些专业问题。
“人口?人口我不太清楚。”赵泗认真的回答到。"
王离的动作很快,不消一会就弄来了不能吃的盐。
赵泗一看王离手里拎的石头,陷入了沉默。
“我让你拿盐来的。”赵泗开口道。
“是啊,不是不能吃的盐么?”王离满脸疑惑。
他拿来的就是不能吃的盐啊,石头和盐结晶混作一块,要不就干脆是山里畜牲舔的盐石头。
“有什么问题么?”王离开口问道。
“是不能吃的盐,但有没有可能这是石头不是盐?”赵泗开口问道。
“兄,这是盐!”荆在一旁小声开口。
赵泗一愣,满脸质疑:“这能叫盐?”
这分明是石头!
“我说的是那种乱七八糟,黑乎乎一大团……”赵泗比划到。
卤盐以及原始杂质较多的盐结晶,才是赵泗要的东西。
“那盐能吃,这盐不能吃,将军没拿错。”荆一脸理所当然的点头。
“吃了会中毒的!”赵泗认真的说道。
“不吃就没盐吃。”荆开口回答道。
“这盐石头也不是不能吃,以前家里实在买不起盐,就会跟着畜牲屁股后面去山里找盐石头,舔着味道也是咸的,就是咬不动。”荆开口回忆道。
盐在这个时代是个稀罕东西,哪有什么不能吃的盐。
咬得动咽得下去那就是能吃,至于吃了嗝屁那都是少数,就算重金属超标说实话也不会吃了就死,大部分情况下会因为重金属堆积累积一些慢性病。
除非严重超标,才会吃了以后直接暴毙。
真暴毙了那就是命不好呗,主打的就是一手靠运气。
赵泗陷入了沉默……那要照荆和王离的逻辑来说,还真没什么毛病。
“那这么说齐地肯定不缺好盐。”赵泗揶揄了一句。
王离当即笑着表示赵泗说得对。
“齐地产盐极多,多数盐矿都在齐地,不过齐地之盐只比井盐便宜一点。”王离开口道。
“那是,那边靠海,天然盐场不再少数。又能煮海成盐,总归是吃不死人。况且煮海成盐,成本太高。”
目前内陆地区的盐的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吃的死人的不卖,吃不死人的接着卖,顶破天把里面的石头蛋子给捡一捡,说不定卖给那群贵人的,也不过是拿筛子筛几遍罢了。
至于齐地之盐,胜再是海盐,重金属不至于超标,又是煮海成盐,成本颇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赵泗也没在跟他们继续纠结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人太乐观了。
吃不死得了慢性病怪自己身体不好。
吃死了怪自己命不好。
嗯……
赵泗已经对这个时代市面上流通的盐有了一些具体猜测。
其中最高端的,质量最上乘的应该是井盐。
井盐一般质地纯粹,杂质较少,味道纯正。
其次就是齐地海盐。
再次之就是内陆地区的盐矿了。
自然盐矿不在少数,海边的天然盐场也不在少数。
然后根据吃得死吃不死划分,吃得死的盐矿就是废矿。
吃不死的那就是好盐矿。
说不定多久吃坏身体也是一种衡量标准,毕竟每个地方的盐杂质含量都肯定不一样。
经过漫长时间发展,大部分可供食用的,质地纯粹的盐产地基本都被各地势力包圆。这个时代的盐也就有了一定的等级之分。
当然,肯定还有黑心的盐商拿着卖不出去的重金属超标的盐继续卖,好盐坏盐掺一起,只要吃不死,价格够便宜,总有人买这玩意。
自然产盐很少有不含重金属的,而这些重金属很多都是不能通过筛子等简单的过滤手段过滤掉的,故而大部分盐矿都对身体有致命影响。
哪怕这个时代卖的盐质量已经很差,但是实际上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
大部分老百姓买不起盐,自然也有自己的生活小窍门。
家里牛羊往山上一放,畜牲这玩意会自己找盐舔。
哪怕是啃不动的盐石头,里面也蕴含一定的盐分,甚至很多家庭还保留着用煮盐石头调味的习惯。
“找那些吃了容易得病,容易死人的盐矿来……”赵泗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如果按照王离和荆的说法,恐怕这些吃了容易得病容易死人的盐矿,也还有很多人在冒着生命危险在吃。
连盐都吃不上了,你跟他们说这玩意有毒,他们也不能听啊。
不消片刻,王离又带来了一堆质地近乎为黑色的盐巴块。
“这玩意就是了!”王离开口说道。
赵泗闻了闻,感觉不像盐,小心翼翼的抿了一点在舌尖。
味道那叫一个五彩缤纷,除了盐味啥都有。
苦,发涩,还有泥巴味,里面还有点金属味道。
“弄些布匹来。”
赵泗又让王离弄来木炭,再找些杂草芦苇乱七八糟的,引燃篝火,烧透以后就是天然的草木灰。
草木灰,木炭!
天然吸附过滤提纯神器!
将卤盐砸碎,融入水中,加入草木灰搅和,再用丝绸包裹过滤,先把不溶于水的杂质过滤掉。
重复几次,基本上没有太多肉眼能够看得清楚的杂质,放入木炭吸附色素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后等待盐水水质变得差不多,就可以直接蒸发析出盐结晶了。
没空等太阳给晒出来盐,直接放入鼎中烹煮,青灰色盐结晶出现。
“青盐!”王离看着最后的结晶,颇觉神奇,围着小鼎转了半天。
这分明就是黑乎乎的卤盐里面弄出来的。
从能吃死人的卤盐,变成上等的青盐?
王离有点不明觉厉。
整个步骤充斥着他看不懂的东西。
不是变成水了么?还加灰在里面搅和,还加木炭。
最后怎么又给煮出来了?
赵泗大概对比了一下,出盐率有点低。只出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除了过滤提纯产生的损耗以外,这一块卤盐,其中的杂质很有可能超过了二分之一!
这压根就不是盐结晶,而是盐于其他重金属乃至于泥土石头等乱七八糟的混合晶体。
“能吃么?”王离看着面前小鼎里薄薄一层开口门道。
“自然能吃!”
荆不假思索的从鼎里捞出一些放入嘴中。
对于他们的船长,荆从不质疑。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出海的时候缺盐赵泗就是这么煮盐出来的。
荆依稀记得当时所有人惊为天人的样子。
“自然能吃!”赵泗笑着开口。
里面还有没有其他重金属了?肯定有。
就这种简陋的过滤手段,怎么可能完全去除重金属?
只不过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经历了草木灰木炭双重过滤以后,基本上是吃不死人了,也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
当然,还想要继续提纯也不是没办法,可以使用饱和结晶法。
这个简单,初中化学就有教来着。
这一顿,始皇帝终究还是没吃太多。
虽然味道是那个味道,评心而论甚至肉更嫩,汤底更鲜,但是食欲终究没有那么旺盛。
始皇帝只是吃了个半饱就吃不下去了,只以为是上一次食欲大开新鲜感作祟,亦或者是心情不同,并没有过多细思。
等待他处理的政务还有很多很多。
而另一边的王离,来到了父亲王贲的面前。
“你同赵泗交好,问一下他可否认识一个名为季泗的童子。年龄应该和他相仿,以前家在下邺。”王贲开口道。
王翦嘱托的事情王贲自然没忘记,书信已经发出,不过琅琊那边有消息的概率不是很大。
王贲估摸着这个名叫季泗的童子要么是压根没回来,要么就是凶多吉少,王贲有印象,赵泗带了一大堆骨灰坛子回来,还曾经委托过王离安置过其中一部分。
家中老爷子难得上心,都这个年纪了,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得办的尽心尽力才行。
“嗯!”王离点了点头,然后出具出营文书。
“出营去何处?”王贲开口问道。
“归家取书,陛下赐赵泗《显学》《五蠹》,赵泗心中向学,欲借家中藏书一观。”王离开口道。
王贲点了点头,父子二人站在原地又没了什么话语,略显僵硬。
“可从家中使女挑些赠之。”王贲沉默半晌开口。
王贲并不算是政治小白,或者说就现在的情况,哪怕是政治小白都知道赵泗的未来一片光明。
不是因为赵泗出海归来,也不是因为赵泗奉上三种新粮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是那一日,始皇帝邀请赵泗同饮同食。
王离也被邀请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王离是王翦的孙子,是王贲的儿子,又恰好是赵泗的朋友。
王贲那一日在旁斟酒片肉,一切经过历历在目。
家中嫡子王离和赵泗的表现可谓是天差地别。
王离面对这样的场景,拘谨不言,虽然同食,却不言不语,始皇帝则少有和王离交谈的时候。
相反赵泗表现很好,不卑不亢,镇定自若,同饮同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趣味横生。
王贲清楚自己儿子王离的能力并不是十分足够。
难得这样王前亲近的时刻,当然希望那个和始皇帝滔滔不绝,喝酒吃肉镇定自若的是自己的儿子。
可惜……
王离再一次辜负了他的期待,哪怕他在旁边耳提面命。
王离依旧放不开手脚。
很显然,赵泗在始皇帝心中留下了名字。
哪怕赵泗现在是微末之身,哪怕赵泗能力有所不足,底蕴不够。
但是能力可以后天学习,当他在始皇帝心中留名的时候,未来就已经注定了一片光明。
简在帝心!简在帝心!
王前亲近是一种极大的殊荣,更不用说始皇帝事后对赵泗的赏赐。
加爵三级,并没有赏赐什么金银财宝,而是赐书,其中期盼可想而知。
不过,若说因此对于赵泗有什么敬畏倒不至于,王家三代人的努力,不是赵泗一代人能够轻易追上来的,王翦的地位本就近乎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不过王贲对赵泗印象不错,王离和赵泗恰好关系也不错,留个善缘。
王贲和同僚的关系算不上特别好,王贲行军和为政都比较独,再加上有一个彻侯父亲,为人又比较沉默寡言,故而没有太多的政治盟友。
但是人情往来,结个善缘,这种微末的道理王贲并非不懂。
王离的能力不够,他需要人情往来。
“送过啦!”王离摆了摆手。
“不过赵泗在咸阳压根没有住宅,就算送了也没地方留,因此并没有要。”王离开口回答道。
王贲点了点头,王离和赵泗关系交好他看在眼里,除了提点意见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有心想要批评一下王离在和始皇帝同饮同食时的糟糕表现,最终又没能开口。
“回去吧……”王贲侧过身子,不再看自己的倒霉儿子。
“嗯。”王离点头欲走。
还以为父亲叫自己过来又要被训上两句呢。
王离挨骂的次数多了,脸皮也厚了,至于挨揍的次数倒是不多,小时候挨了几顿揍以后,远在老家的爷爷王翦亲自赶来给了王贲一顿老拳,王离就再也没挨过揍了。
“代我向大父问安。”王贲又开口道。
“好!”走到门口的王离开口回答,脚步一下没停,一溜烟的跑出去。
虽然和父亲王贲有些疏远,不过王离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起码自己的朋友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不然父亲也不会说出遣家中使女相赠的话。
一溜烟拍马赶回家里,回去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黯淡了下来,王离有蓝田大营开出的验传,故而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一路畅通无阻,赶至家中。
“大父可曾睡下?”王离开口向奴仆问道。
“不曾,主人正在屋里等您回来。”奴仆开口回答道。
王离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大父怎知我今日归家?”说罢,脸上带着将信将疑来到屋内,果然只见大父靠在床头,一旁两个使女捧着暖炉给王翦烘脚揉腿。
王离自顾自走进去行礼:“大父怎知我今日归来?”
说罢不顾已经跪伏在一旁地上青春靓丽的使女,来到王翦身前接过了使女的活计,为王翦揉腿。
“下去吧!”王翦摆了摆手,两个使女这才行礼告退。
王离则乖乖跪坐在床边为王翦揉腿一边揉腿一边问道:“大父,使女可有我按的舒适?”
因为王翦打小就宠溺王离,王离又基本上都跟着王翦住在老家,故而只有在爷爷王翦面前,王离才会显得更加自然活泼,和在王贲面前的闷葫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各有各的好处~……”王翦打了个哈哈,吭哧吭哧着起身换了个姿势,半躺在床上享受着乖孙的按摩。
“那不如孙把使女再唤来,两样好处全占了才好。”王离笑着开口说道。
王翦半眯着眼睛,伸出一只手来摸到王离的脑袋,尔后两指一并屈指为凿,落在王离的脑袋上。
王离适时抱住脑袋开口:“大父,你还未说怎知我今日归来的!”
(月票推荐票快捷通道)
和赵泗的谈话让始皇帝总的来说,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
毕竟赵泗不是专业的,他只是一个拥有一定海上航行经验的现代人,不是专业的地理学家,也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赵泗只是给始皇帝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但是门里面究竟有什么,赵泗自己都不清楚,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不可能对这个时代的世界侃侃而谈。
大秦想要了解世界,还需要继续探索,需要派遣出去一艘更加全面更加专业的船队。
需要派遣大秦官方的使者和世界建立联系,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国家,这些国家究竟是怎样的政权结构,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产业,多少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评估出来,大秦能否在海上获取利益,大秦开海能否作为未来的方向。
至于制盐之类的发明以及三种新粮的具体种植方式的事情始皇帝反而没有多问。
不是不重要,而是始皇帝和赵泗的交谈中明显能够感觉出来赵泗的生嫩。
赵泗的政治素养是处于相对荒芜的状态的,换句话说,目前的赵泗并不具备详尽汇总汇报能力,始皇帝想听的东西从赵泗嘴里说出来会很碎很杂,聊天讲故事可以,汇报工作的能力,赵泗还差的很远。
这很正常,赵泗就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理解的谈话重心和政治人物理解的谈话重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赵泗穿越而来就在海船之上,归来以后这才多久?怎么可能具备政治素养?开玩笑,赵泗连个班长都没当过,当过最大的官就是劳动委员。
始皇帝将问题抛给了王贲,王贲作为蓝田的最高负责人,自然是有义务有能力汇总赵泗的一应事物。
而王贲也接住了这个问题,他早就准备好了一系列文书记载,从红薯土豆的育种方式,到晒盐法的成本,精细到用了几个人,工作了多久,消耗了多少草木灰,产出了多少盐。
其中自然也夹杂着赵泗从王离那里讨要军匠,弄出来的一些小发明,具体经过,由谁制作,图纸……全部都有备份。
很显然,王贲这个老父亲为王离操碎了心。
这些事情本来都应该是由王离来做,王离并非没有做,但是做的不够详尽,有些东西王离压根就没写,如今如此详细的汇报汇总,全是王贲独自补充。
赵高一摞一摞的将竹简缣帛搬上始皇帝的副车,这时代竹简写字确实不方便,字数但凡多一点,汇报但凡详细一点,一个竹简都不够用。
始皇帝一天批阅一百多斤的竹简并非无稽之谈,现实不像是电视剧,地方官员廖廖几笔寥寥几句就将一地民生总结殆尽。
天下事何其繁多,始皇帝又事必亲躬,而如赵泗这般颇受重视者,弄出来的东西又不少,全面介绍下来,好几捆竹筒是正常现象。
“辣椒孜然这些香料可还有留存?”始皇帝看向赵泗开口问道。
今日可算是给始皇帝吃了个尽兴,小火锅吃着,小烤肉吃着,小酒喝着,还有赵泗在旁边讲故事。
这也让始皇帝这个并非老饕之人意识到这些海外香料的美味。
始皇帝并非老饕,但是长久以来食欲不振也不是一个办法。
连夏无且都一时半会不知道该如何调理,可是不能总是如此,吃东西都吃不下去,如何养的好身体?
若有辣椒孜然这些香料辅助,自己在宫里煮点小火锅什么的,总有些食欲,能吃的下去东西,身体才能够好起来。
“有的,不过剩的不多了。”赵泗嘿嘿一笑说道,之前赵泗没咋吃,因为实在没食材,摊上王离这个狗大户一样就不一样了。
王离可以说是要啥有啥,想吃啥肉王离都能弄来。
俩人那是嘎嘎一顿炫,留下来的辣椒等香料加起来也就剩个十来斤了。
“予朕拿一些。”始皇帝开口道。
赵泗应声,只是去拿的时候却犯了难。
这拿一些是拿多少?自己可就剩十几斤了。
思来想去,赵泗干脆留了两斤左右的香料,剩下的全部给始皇帝送上。
赵高接过赵泗奉上的香料,一并装车。
“大部分都已经种入地里,民这里只有这么些了。”赵泗开口说道。
始皇帝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赏赐赵泗,而是示意王贲于自己同乘一车离开赵泗王离二人所在的军所。
可能是直接回宫了?也可能是跟王贲再谈点别的什么事情?
赵泗也不知道,他又看不到,而且吃饱喝足,始皇帝来了之后酒又喝了不少,他头也比较晕,人也比较困,此刻也懒得想这些东西。
倒是王离,此刻显得颇为亢奋,两只手把住赵泗的手上蹿下跳。
“你干嘛~~”赵泗被王离拽了一个趔趄,好悬没哎呦出来。
“兄!托你的福!”王离兴奋的开口,脸上的表情生动活泼。
“嘿!我爹亲自给我斟酒片肉!”王离一边说一边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笑容。
“兄!”
“我爹对我可是非打即骂,少有好脸色!”
“便是同僚之间,也颇为肃穆,少有笑容,臣属皆畏我父!”
“不亲民?”赵泗晕乎乎的问了一句。
“甚是亲民?”王离愣了。
“我听说名将治兵,皆同袍,同寝,同食,吴起为士卒允创,士则有敢战效死之心。”赵泗回答道。
“我父才不如此,他治军向来严谨,不苟言笑。”王离说着说着又摇了摇头。
“不是说这个,我父亲自为我斟酒煮肉啊!”王离兴奋的要蹦起来。
“以前没这么过?”赵泗开口问道。
“打我记事以来肯定没有。”王离信誓旦旦的说道。
“那可能在你记事之前,毕竟是你爹。”赵泗开口道。
“不是!不是这个!”王离说话有点大舌头。
“我父只有对大父才会如此!嘿!”
从来没享受过的待遇让王离有些飘飘然,王贲始皇帝在的时候王离就像一个卑微的小透明,二者一走,王离就显得鲜活透明起来。
“你是想说,你今日像你大父一般?”赵泗脸上露出几个问号。
“嘿嘿……嗝……”王离晕乎乎的靠在赵泗身上,也不说话,就是脸上还带着傻笑。
“嗯……”始皇帝允许了蒙毅的请求。
盐,从来都是国之重器,晒盐法将制盐成本进一步压缩,制盐效率进一步提高,但是缺点也变得显而易见。
在晒盐的过程中,只要天气不好,前面的所有工作都会变成无用功。
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天气预报,但基本上诸子百家皆对天气有一定的研究,而阴阳家则是其中造诣最为深厚者。
蒙毅点了点头继续汇报。
“制一犁,辕曲,耕种之时,事半功倍!”
“制一尺,使之精效准确!”
蒙毅念着念着自己反而有些好奇起来了。
蒙毅的好奇并非毫无根源,而因为蒙毅治墨。
他本就是一位墨者。
一个合格的墨者必定是知道一定的工具制作的相关道理的。
因为这玩意在墨家经典上是绕不过去的,只不过有的擅长有的不擅长罢了。
当然,墨子千古以后,墨家迄今为止已经一分为三,匠巧制作完全不学,只钻研经义理论的墨者也不是没有。
蒙毅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墨者。
他的匠巧技术属于这个时代墨者的平均水准,对大部分技巧以及原理都有所学习。
故而在看到赵泗弄出来的一些颇为实用的小发明之后,蒙毅倒是来了一些兴趣。
曲辕犁放在历史长河之中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放在当前这个时代只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发明。
实在是这个时代较为原始,百姓普遍没什么积蓄,天下普遍还在使用较为原始的耕种方式,除了关中之地耕种模式受大秦国制影响普遍比较成熟普遍开始使用耕牛套犁以外,其余地区一言难尽。
总之意义在这个时代确实没那么大,想要曲辕犁普及天下,前提是大多数个体农耕户能配置的起耕牛曲辕犁。
不过短曲辕犁人力也能拉动,制作成本也就没那么高,比起来耒耜这种较为原始的耕种方式,人力拉动短曲辕犁耕种,也并非不能推广普及,耕种效率肯定会有所提升。
赵泗压根没考虑过以人为畜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的思想有所影响,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这个时代缺乏认知。
难道使用耒耜就不算以人为畜了?
蒙毅不同,他看到王贲汇总的具体经过,以及大小曲辕犁的表现,第一时间就敏锐的捕捉到,小曲辕犁虽然效率低相对来说,但是有可能人力代替畜力。
牛这玩意忒贵,不是以人为畜不为畜的事,是实在用不起耕牛时的一种补充。
不过因为王贲并非专业人士的原因,记载数据也以询问军匠为主,故而其中一些关键地方还需要蒙毅去亲自考证才能确定自己想法是否正确。
因为王贲只记载了先弄出来了小曲辕犁,后弄出来了大曲辕犁。
而赵泗也压根没提小曲辕犁是否具备可以以人力代替畜力属性。
至于其余的游标卡尺锉子刨子等小工具,却先被蒙毅放在了一旁。
“怎么?”始皇帝见蒙毅话语之间有所思考,开口问道。
“这曲辕犁臣倒是有些想法。”蒙毅皱眉开口。
“如何?”始皇帝示意蒙毅发炎。
“此曲辕犁先制出的是小犁,尔后和直犁对比以后,效率不及大犁,又制出曲辕大犁。”
“只是大犁沉重,不以畜力难以耕种,小犁轻巧,却不知人力能否拉动。”蒙毅开口道。
始皇帝拿过竹简看了一遍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若这小曲辕犁能够以人力使用那就真的可以推广开来了,小犁造价成本虽然也不会低,但是不会高到像大犁一般令人难以接受,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畜力,还能提高耕种效率,百姓没有道理不使用。
“若此犁能用,需得计算出来,各地核考也要重改。”始皇帝开口道。
眼下的大秦各地官员都是有考察制度的,作为耕战体系的国家,地方产粮的多少对官员的业绩考核影响很大。
基本上上到官员,下到黎民,大秦都有一个成体系的奖惩系统。
作为一个自耕农,假如你耕种得力,缴纳的赋税比旁人多,种地产量比别人高,是可以获得实打实的爵位奖励的。
是真金白银直接落实到个人的。
作为一个官员,假如当地的粮食过低,而说不出什么所以然的情况下,是会直接判罚判责的。
秦国的税收很重,处罚很严,但是同样奖励也很到位,哪怕是饲养的耕牛每年都有耕牛选美大赛,照顾的最好,最健壮的耕牛,都能够获得一定的赏赐。
如果你的耕牛消瘦,还会有当地里长专门谴责问询。
当然,这些描述的是一统天下以前的大秦。
完善的奖惩制度的维护需要足够的有素质有素养有能力的庞大的吏员规模来支持,而目前一统天下的大秦,摊子一下子铺开数十倍之大,吏治相对来说有些败坏。
这个败坏程度是以咸阳关中为放射圈,咸阳,关中地区,吏治依旧清明,奖惩制度依旧完善,越远,吏治情况越差。
这么说吧,张良要是个关中人士,想刺杀秦始皇,可能没行动人就被扭送官府了。
而在博浪沙刺杀的张良,却能够逃之夭夭。
总的来说,大秦吏治因为摊子铺的太大很多东西放眼天下只能停留在书面上,是落实不到关中之外的地方实际的。
但是粮食产量,作为考核的核心标准之一,肯定是全国通用的,如果曲辕犁能够人力使用,普及到千家万户,具体的考核业绩标准肯定还要重新调整。
这样一来,想不推广的也要推广,不推广考核压根不可能达标,因为新的考核标准就是按照曲辕犁推广以后的产量直接制定的。
不过落在实处,始皇帝更在意的还是畜力耕种,耕牛普及。
一项小工具只能略微提升一定的粮食产量,六国地区的粮食产量和关中地区的差别太大了。
跟地理因素反而没太大关系,秦地苦寒那是春秋以及战国初期公认的事实,现在关中作为天下粮仓,也是秦人几百年修建渠道,刺激生产,改革吏治法制做到的。
六国很多地区气候比关中更加宜人,自然条件更好,但是粮食产量反而被关中甩开一大截。
很显然,刚刚被征服的六国之地,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也还有很长。
人力肯定不如畜力!
哪怕有了可以人力耕种得曲辕犁,大秦依旧要走耕牛普及的路线。不能因为一个可以人力使用的曲辕犁而本末倒置。
耕牛犁种不能普及,天下就不能如关中一般。
(短曲辕犁可以人力耕种,有文献支持,不贴了。水田不太能行,有点够呛,
人力耕种曲辕犁在本书不会大书特书,主角,蒙毅,始皇帝,是三个层次的思考。
主角的认知固有停留在短曲辕犁现在不如长曲辕犁,曲辕犁也没有普遍推广的基础,因为除了关中地区,其余地区耕牛耕种做不到普及百姓。
蒙毅认为短曲辕犁具备人力代替畜力的可能。
始皇帝认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不会因为曲辕犁的出现而改变大秦目前推广农耕的战略步骤和路线。
事实上,封建时代,如果人力广泛代替畜力并且成为长期的主流现象,一定是朝廷出了问题。)
红薯和土豆都不挑地,适应性极强。
对水肥要求不高,贫瘠的土地也能种,在盛世年间,多种于地头田埂,犄角旮旯也都能种。
若是遇上了灾荒,更是能够成为救命粮,近代饥荒年代,若是没有红薯土豆,都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不过这两类作物都有一个问题,不易储存和运输。”赵泗认真的说道。
相比较于粮食,红薯和土豆的储存条件更高。
古代倒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通过挖掘地窖的方式储存红薯土豆也不是不行,只是储存期和粮食比起来相去甚远,稍有不慎就会发芽变质。
红薯还好,发芽以后还可以吃,土豆发芽以后甚至会产生毒素。
而在运输流通方面,也明显不如粮食,对于运输条件要求更高,很难进行远距离流通。
“此二类不同粮食,储存下来稍有不慎就会发芽,如这红薯,发芽了也还能吃,这土豆发芽了以后可就有毒了。而且长期食用红薯,还会烧心胀气。”赵泗开口解释道。
赵泗只是隐约的记得红薯产量比土豆高很多,但是土豆后世好像反倒即将成为第四主粮,红薯倒是一直只能作为农副产品。
赵泗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长期食用土豆不至于像长期食用红薯那般难受。
赵泗小时候是真连着吃过半个月红薯的,难受是真的难受,红薯叶,红薯藤炒菜,红薯干炖汤,烤红薯~~
而且口感上来说土豆比红薯好的多,现代的蜜薯大多是改良后的品种,正儿八经没有经过人工培育的红薯,纤维很多,吃起来塞牙。
相比较之下,这两种农作物和主粮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土豆差距小一点,红薯差距大一点。
不过红薯产量更高,土豆产量略低。
至于如何取舍,那就是始皇帝的事情。
始皇帝闻言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不易储存,运输条件相对比较苛刻。
光这两个条件就会让这两种农作物的评价降低很多。
古代运输速度本来就极慢……一来一回,运输的时候储存起来费事,运输又费时,很明显不适合作为主粮进行耕种。
但是那可是亩产五百斤……
哪怕作为农产品的补充也是极好的。
站在秦始皇和市场经济的角度上来看,主粮的地位不可取代。
粮食一旦流通起来,就具备了商品属性,而土豆和红薯的商业价值极低,但它们的高产在古代能够作为兜底的存在。
这就够了!
民以食为天!
尽管这个时代尚未提出什么民为水君为舟的话,但是始皇帝也明白,下层趋向于稳定,上层的统治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再退一步说,发动徭役,战争,等大量耗费人力物力的事情的时候,有亩产高达五百多斤的农作物,下层的承受能力也随之大大增加,更不易发生混乱变动。
从长远角度上来看,这是增加大秦底蕴乃至于动员力加固大秦统治的东西。
尽管赵泗已经往少了说了,尽管赵泗已经提前说了红薯土豆的弊端,但是始皇帝依旧显得十分郑重。
“那此物呢?产量几何?”始皇帝指向玉米,语气中多了几分期待。
“略高于五谷……可为主粮使用。”赵泗沉吟片刻后说道。
赵泗还真就不知道玉米的产量具体多少,他只是大概知道,玉米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能够高于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具体高多少他还真不清楚。
“不过此物生长更甚于麦,气候适宜,百天即可长成。”赵泗开口回答。
乍听赵泗说过亩产五百斤的土豆红薯以后,始皇帝听到略高于小麦的玉米第一时间竟然有些失落。
可是听到从种下到成熟只需要百来天,始皇帝立刻就提起兴趣。
始皇帝可不是不通五谷之人,大秦本就是耕战之国,作为一国之君若不知农时可就贻笑大方。
眼下五谷,麻、黍、稷、麦、菽。麦是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
麦的成熟期基本上要两百多天,倍多于玉米。
一般情况下都是两年三熟,极少数气候宜人方便灌溉的地区是一年两熟。
或者就是一年之中,种完麦之后穿插种些其余农作物。
在赵泗口中,玉米的亩产量虽然只是略高于麦,但是生长时间却只有麦的一半。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做到一年两熟。
种一茬小麦,再种一茬玉米,一年丰收两次。
二者补充种植,推广开来,大秦的粮食年产量不说翻倍,起码也能增长个一半。
“嗯……有何缺陷?”始皇帝下意识的看向赵泗。
他下意识的认为这样的农作物也有一定的缺陷,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十全十美。
“嗯……没那么好吃?”赵泗开口。
不过仔细想想,在这个脱壳技术有限的年代,貌似带壳的小麦煮出来未必有玉米口感更好……
在精米精面出现之前,玉米成为主流农作物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始皇帝微微一笑。
没那么好吃?粮食能好吃到哪里去呢?
方便储存,吃起来不会得病,能够远距离运输,产量足够,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满足了成为主粮的硬性标准。
“那此物?”始皇帝看向红彤彤的辣椒。
“产量几何?”
赵泗摇了摇头。
“陛下,此物并非粮食,而是香料,比之麻椒,风味更甚,食之甚美,欲罢不能!”赵泗开口道。
麻椒原产地在秦岭附近,属于诸夏文化圈,只不过产量有限,属于极为贵重的食料,甚至价比真金白银。
不过,但凡古代,香料就没有便宜的。
很长一段时间,香料的价格都是个黄金挂钩。
历史上中东某些国家,因为几颗胡椒树的归属发动举国之战也是时而有之。
面对一车香料,中东番邦小国的国君甚至能撕下脸皮当场扣押,如同盗匪。
但是,作为一个无辣不欢之人,相比较于其他香料,辣椒才是赵泗的最爱。
(注:稻多种于南方,秦朝时期南方尚未开发,故此时五谷,有麻无稻,至宋后,南方得到开发,稻成为主流粮食,稻才取代了麻的地位成为五谷之一。)
这个时代条件有限,没有科技弄不出来特别可口的食物,毕竟赵泗不是什么大厨。
炒菜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不过这个时代制造铁锅貌似还有技术壁垒尚未攻破?
赵泗王离二人闲聊之间,小鼎沸腾。
锅里辣椒麻椒牛骨菌子上下翻腾,有菌子的鲜味,牛骨头的香味,辣椒和麻椒的麻辣,顺着水汽不断上浮。
将案几上摆着的形状如同虎蹲一般的形盐掰开一块一块的放下,待融化开来以后,用羹勺尝试咸味是否适中。
美妙的味道在口中绽放开来。
香!
理智上来说赵泗清楚自己捯饬出来的没有科技于狠活的火锅肯定比不上现代的工业化火锅。
但实际入口,只让赵泗恨不得吞下舌头。
盖因为来到这个世界食物太过于匮乏,还是头一次尝到味道这么正的东西。
“好了!可以置肉了!”赵泗拍手!
王离迫不及待将仆从片好的牛肉羊肉分开放入,赵泗又置入一些青菜菌子。
二人满怀期待的等待着锅里的食材逐渐上下翻滚,牛肉逐渐变色。
牛肉片的不算很厚,薄薄一层,鲜牛肉,没有冷冻,熟的也很快。
赵泗习惯吃熟透了的东西,没有立刻捞出,王离已经迫不及待的将煮好的牛肉捞出。
肉香味,从未闻过的辣椒味,搭配上麻椒,菌子的鲜,骨汤的香,全部汇集在这一片小小的牛肉之上,味道直冲王离肺腑。
急不可耐的放入口中,各种香味自口中散开,伴随着咀嚼又融合交汇在一块,让王离口中生津。
“香!”王离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想不到如此吃食,竟然能够美味至此!”
秦朝时期的煮,其实就是火锅的前身。
老北京的涮铜锅,意义都差不多。
无非就是火锅有锅底,古代哪有人去捯饬锅底?
骨汤肉汤肯定有,但是没有搭配辣椒麻椒菌子这些香料,食物在里面一煮煮上许久,吃起来的味道可就差远了。
“同食同食!”王离招呼赵泗,二人一同食之。
火锅的香味遮住了麻辣之味,赵泗是好辣之徒,放的辣椒麻椒不在少数。
王离初吃只觉得辣椒和麻椒对味蕾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吃上一会只觉得嘴巴麻木。
可偏偏那种令人愉悦的味道在舌尖味蕾又仍在不停的绽放,令人欲罢不能。
赵泗也是如此。
辣本身就是一种痛觉。
吃辣也本身就是为了享受味蕾被刺激被动分泌的愉悦因素。
赵泗和王离两位都是合格的老饕。
你一口我一口,牛肉羊肉纷纷落入锅中。
原本二人是一人一鼎,分案而坐,还有些不太熟悉人面前的矜持。
因为捯饬火锅的原因,只能用一个鼎煮,二人就从原来的一人一案变成两人一案。
两个人隔着小鼎相互对坐,乘着食材案几被二者推到一旁而不是摆在面前。
之前都是正襟危坐的跪坐姿态,眼下二人皆是盘膝而坐,你一口我一口好不快活。
王离甚至都没有空隙和赵泗闲聊海上的事情,只有在等待食材煮熟的间隙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赵泗聊天。
这锅是越煮越辣,俩人也只觉得越吃越香。
甚至二人的嘴巴都已经完全麻木发胀,不过二人都并不在意。
赵泗看到王离的嘴巴已经肉眼可见的胀大,赵泗估计自己也差不多。
不过无所谓,形象?形象是什么东西?
不过嘴里辣喝水就多,一旁用小壶子盛着的酪浆早已经被喝完,现在换上的是一种新的饮品。
一种不知名果子的发酵物,也是没有酒味,以酸为主,后味比较甜,味道是比较清香的味道。
赵泗还挺喜欢喝这个时代的饮料的。
味道属实不错。
包括酒类。
这个时代的酒大部分以米酒黄酒果酒为主,而并非白酒。
度数不高,还有粮食味道,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很难喝醉相比较于酒水更像是一种饮料。
得亏不是酱香科技,若不然赵泗少不得头疼一番。
赵泗和王离两个老饕一边吃一边喝,很快二人案几上的牛羊肉被横扫一空。
置于鸡肉?
正经人吃火锅谁吃鸡肉啊?
王离放了一块,尝了尝,味道一言难尽,比起来牛羊肉差了老鼻子远,也就置之不理了。
青菜也被讲究营养均衡的赵泗扫荡完毕。
王离平日里也是食量惊人之辈,可是现在竟然吃的肚子溜圆,撑得不行,以至于正襟危坐都有点不舒服,得一只手向后撑着把肚子释放开来。
赵泗差不多也是这个形象,他吃的也不比王离少。
眼下二人,都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两只手向后撑着,两边是一片狼藉的案几,看起来没有任何风度可言。
赵泗注意到了王离如此的模样,又看到王离肿胀的嘴唇。
红彤彤厚厚的大嘴皮子,配在任何一张脸上都很喜感。
王离看赵泗也同样如此。
二人相互打量对方,王离最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不雅,相比较于赵泗,王离更多的受到了这个时代礼仪规矩的熏陶,本想即刻调整,又注意到赵泗同样如此,再一看赵泗性感的大嘴皮子,怎么都严肃不起来,一张嘴哈哈大笑,两张大嘴皮子上下蹦哒。
赵泗一看也蚌埠住了,二人相互指着对方开口大笑。
笑了一会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停下吃食以后,对味觉的香味刺激停了。
麻椒辣椒的后劲没了食物的掩饰,一股脑的涌上来。
赵泗只感觉自己的两片大嘴唇子都不是自己的,摸上去都没有啥感觉,嘴巴里不断口水,舌头辣的在口腔顾涌。
王离也是差不多的状态,大口喝水喝了几口,肚子撑得又实在喝不下去,打眼一看赵泗正在吸溜吸溜的在那大口吸气吐气,一只手在嘴巴旁边不断煽动。
嘶!哈!嘶!哈!
王离也跟着模仿,嘴里果然舒服了很多。
只是一时不备,嘴巴里因为不断的麻辣刺激分泌的晶莹口水顺着嘴角泄出一坨滴滴答答的落在衣服上地上。
赵泗正在吐气,张着大嘴流口水的王离,大笑了起来。
王离的形象,逐渐被他撕下标签,而活生生的在他脑海里回应。
(求追读!)
这玩意真是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谁没事学这个啊?赵泗知道的也就是含碳量影响钢铁质量,再多的就不知道了,他甚至连铁的熔点都没记住。
钢铁取代青铜器是大势所需,没办法,铁矿的开采难度远低于铜矿,其次铁的蕴藏量远高于铜的蕴藏量。
最后,封建时代的巅峰钢铁铠甲武器质量远胜巅峰青铜器。
问题出在这里,秦朝已经是青铜器巅峰了。
而钢铁冶炼甚至连入门都不算……
这边科技树已经点满,那边科技树刚发了个芽,而钢铁冶炼如果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技术进展慢的令人发指。
汉朝铁器逐渐取代青铜器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因为铜矿越来越少,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另外大量的青铜器以及金银被陪葬,铜还要承担货币属性,完全不够用,没办法才去点了铁器的科技树。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技术断层!
秦朝的青铜冶炼水平几乎是青铜器时代的巅峰,秦末乱世,冶炼技术倒退,关键技术和制度遗失,也是汉朝不得不点铁器科技树的重要原因。
而秦朝虽然也面临了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汉朝时期那么严峻,毕竟这个时代还较为原始,商业也并不发达。
青铜,虽然贵且少,但是放眼国家层面勉强还算够用。
而钢铁,以目前表现出来的冶炼难度和令人泪目的实用水平,对于始皇帝而言,还不如继续在青铜器冶炼方面深造,寄希望于找出更大的铜矿和更先进的冶炼技术。
但是赵泗知道,秦朝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走到头了,再往上也就那样。
可惜,想要在这个青铜器质量正值巅峰,数量也勉强够用的时代另开钢铁支线,需要的魄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钢铁冶炼可不像造纸,随便找几个匠人就能慢慢琢磨。
这玩意,投入大的离谱,非得是官方机构大笔大规模投入资金,从铁矿等源头产业开始投入。
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面临很长一段时间负收益的情况。对财政造成极大的负担。
初期的铁器绝对比不上青铜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也不知道始皇帝有没有魄力进行产业转型,这玩意真的是利在千秋!”赵泗琢磨着,哪天撺掇一下始皇帝,顺嘴提上那么一句。
钢铁冶炼技术没有发展,很多东西都无计可施,钢铁性能远高于青铜,这是事实。
正在思索如何撺掇始皇帝投一笔大的,却看见王离一脸喜色的捧着一口青铜锅晃晃悠悠的走来。
“你说的锅,我差人弄出来了!”王离喜气洋洋的拍了拍锅底笑着说到。
得益于赵泗心心念念的炒菜,给王离抱怨大秦没有锅,王离记在心上,作为老饕的王离自然也想尝尝赵泗所说的炒菜是何滋味,于是差使家中匠人按照赵泗的描述制出铜锅。
赵泗入手,沉的离谱。
不过厚度倒是适中,不算特别厚,但是也做不了特别薄。
青铜这玩意脆,弄太薄了不行,天生比铁锅得厚上几分。
王离弄来的铜锅能成这个样子已经十分不错,虽然有可能会影响导热性,但是问题不大,火力全开,锅还能凉了不成?
不过很显然,这口铜锅肉眼可见的价值不菲技艺精湛,在这个时代压根不可能大规模批量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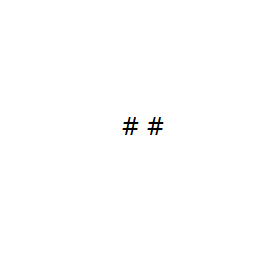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