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小陈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唐瓷年代小陈热门无删减+无广告》,由网络作家“房三善”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只留带皮的边角料。<真正的较量藏在细微处。每逢周三“改善日”,谢师傅会在菜盆里埋几块炸鱼块,却故意手抖让鱼块滑回盆底——直到我们学会用搪瓷盆轻磕窗口,他才笑着多舀一勺。黄阿姨则趁谢师傅熬汤时,往我们碗里多撒把虾皮,末了叮嘱:“莫要告诉老谢,只说汤里的‘固体’自己长了脚。”那个秋雨绵绵的傍晚,小李出差归来得晚,食堂早已关门。我们正欲泡方便面,谢师傅却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个用毛巾裹得严实的搪瓷盆:“热乎的豆角焖面,你黄阿姨特意留的。”掀开盖子,蒸汽混着肉香扑面而来,面条底下竟藏着两块完整的红烧肉——那是招待所用剩的边角料,他偷偷攒了三日。发薪日成了食堂的“节候”。每月初九,我们将饭票钱凑齐,用信封装了塞进谢师傅的白大褂口袋。他总推搡着:“...
《唐瓷年代小陈热门无删减+无广告》精彩片段
只留带皮的边角料。
<真正的较量藏在细微处。
每逢周三“改善日”,谢师傅会在菜盆里埋几块炸鱼块,却故意手抖让鱼块滑回盆底——直到我们学会用搪瓷盆轻磕窗口,他才笑着多舀一勺。
黄阿姨则趁谢师傅熬汤时,往我们碗里多撒把虾皮,末了叮嘱:“莫要告诉老谢,只说汤里的‘固体’自己长了脚。”
那个秋雨绵绵的傍晚,小李出差归来得晚,食堂早已关门。
我们正欲泡方便面,谢师傅却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个用毛巾裹得严实的搪瓷盆:“热乎的豆角焖面,你黄阿姨特意留的。”
掀开盖子,蒸汽混着肉香扑面而来,面条底下竟藏着两块完整的红烧肉——那是招待所用剩的边角料,他偷偷攒了三日。
发薪日成了食堂的“节候”。
每月初九,我们将饭票钱凑齐,用信封装了塞进谢师傅的白大褂口袋。
他总推搡着:“不急,等月底一并算罢。”
可我们知道,他抽屉里压着儿子的学费单,截止日就在每月十五。
有次老张多塞了五元,说是“提前预支改善费”,谢师傅却红了脸:“使不得,你们年轻人还要攒钱讨媳妇。”
十月底忽生变故,陈胖子宣布招待所要扩招临时工,食堂场地须得缩减一半。
谢师傅蹲在灶台前抽了半宿烟,烟头在黑暗里明灭如萤火。
次日,我们见食堂的桌子挪到了走廊,蓝白格子桌布换作旧报纸,谢师傅的菜盆却依旧摆得齐整,每盘肉片底下藏着焯过水的豆芽:“这样看着多些。”
他挠着头,像是做错事的孩童。
作为回礼,我们帮谢师傅干起杂活。
老张用废木料搭了防风棚,小李从码头带回半袋海盐,我将母亲寄来的豆腐乳分了半罐给黄阿姨。
一日,谢师傅的儿子来送伞,我们见那孩子穿着打补丁的校服,却捧着全班第一的数学卷子——方知谢师傅每日多给我们的半勺猪油,原是从自家炒菜锅里省出来的。
天气转凉,谢师傅在食堂门口种了棵桂花树。
他说:“等开花了,摘来腌糖桂花,煮粥甜得很。”
我们蹲在旁边培土,黄阿姨忽然道:“老谢年轻时可是国营饭店的大厨,为了照顾生病的老娘才来此处。”
话音未落,谢师傅已端出刚出锅的辣椒炒肉,油
知道,他是放心不下四个光棍的肚皮。
停伙前一日,谢师傅打开食堂储物柜,里面半袋米、三根蒜苗、半罐猪油码得齐整:“省着吃,黄阿姨明日也歇班。”
又塞给我一张纸条,铅笔歪扭画着电饭煲煮菜图:“腊肉要先蒸,蒜苗炒到半焦再下饭……”末了摸出个塑料袋,里面是晒干的橘子皮:“煮汤时放两块,去腥味。”
那纸条边角卷着,像是被他反复揉过又展平的。
谢师傅走后,食堂铁门挂了锈锁,像道结了痂的伤。
头日中午,我在宿舍门口生煤炉,表哥送的旧电饭煲蹲在小马扎上,锅底还留着去年熬粥的黑印。
蒜苗在菜板上切得咔咔响,腊肉是母亲秋天寄的,藏在枕头下用报纸裹着,切开时油花顺着刀缝往下滴,倒像是时光在流泪。
小陈端着空碗从对门晃来,鼻尖冻得通红:“给点汤呗,我煮的白粥能照见人影。”
他碗里的粥稀得能映出窗外的屋檐,倒衬得我锅里的蒜苗炒腊肉格外奢侈——其实就几片肉,在青蒜里打转转。
正分着,小李推门进来,怀里抱着半只腊鸭:“车上老大送的,说抵饭钱。”
那腊鸭冻得硬邦邦,却让屋里添了些活气。
那只电饭煲成了我们的“灶王爷”。
煤炉太小,锅底总糊,我们便轮流守着:老张切菜,将冻硬的白菜帮子片得薄如蝉翼;小李在走廊尽头洗腊鸭,冰水将手指冻得通红;我盯着电饭煲,看米粒在沸水里翻跟头,恍惚间竟想起老家的土灶。
有次水放多了,米饭成了粥,老张灵机一动,掰进腊鸭骨头,撒把盐和胡椒粉,竟熬出乳白的浓汤,香气顺着门缝往外跑,引得来二楼的王科长探头:“你们这儿搞流水席呢?”
还摸出瓶豆瓣酱,说是爱人腌的。
最艰难是谢师傅迟归的那周。
天气预报说有冻雨,我们囤的米缸见了底,蒜苗早蔫成草绳,只剩几根皱巴巴的芹菜。
小李翻出压箱底的方便面,三包调料掰成四份,老张将搪瓷盆洗了又洗:“煮‘豪华版汤面’。”
正发愁,小陈举着塑料袋冲进来:“我表哥捎的红薯,烤着吃!”
走廊尽头的煤炉成了烤炉,红薯埋进热灰里,甜香慢慢渗出来,小李剥了皮分给大家,热气在他睫毛上凝成水珠:“小时候家里
数比我们外勤还多。”
正说着,谢师傅端着菜盆出来,蓝布围裙兜着的裤脚沾着煤灰,镜片蒙着白灰,倒真似从烟囱里钻出的,竟有几分《追捕》里横路敬二的憨厚。
头顿午饭是白米饭配冬瓜炒肉片,肉片薄如蝉翼,在青灰色冬瓜块里若隐若现。
老张以筷尖戳了戳盘子:“看这肉片,比小李的办案卷宗还薄几分。”
话未落,邻桌传来搪瓷盆磕在桌上的声响,几个穿制服的科员正将海带汤里的豆腐块往碗里拨,汤面油花寥落,倒像是被风刮散的星子。
及至月底,果然生出事端。
陈胖子抱了算盘坐在招待所门口,阳光将他的秃顶照得发亮:“四位同志,这个月的饭勾——”他以肥短的手指敲了敲登记本,“老张廿八勾,小王卅二勾,小李十九勾,加上这位新来的廿六勾,共百又五勾,每勾一元二角,总计百廿六元。”
我捏着工资条的手发紧。
二百一十元的薪水,寄去百元给弟弟,余下一百一十元,扣除饭钱竟倒欠十六元——更不必提日用品与偶尔的人情往来。
老张当场拍了桌子,铝制饭盒盖蹦起砸在地上:“合着我们吃的是金米不成?
上月局里接待财政局,十人八菜一汤才五十勾,我们四人喝粥竟要百廿六元?”
是夜,四个光棍挤在顶楼阳台议事,蚊香在脚边蜷成灰蛇。
夜风挟着梅江的潮气,却吹不散满心的焦灼。
小李刚从码头蹲点归来,裤脚沾着煤渣,抚着肚子道:“昨日在船上啃了三日馒头,如今闻见海带汤味便作呕。”
老张踢翻个空酒瓶,玻璃碴在月光下闪得刺眼:“与其给招待所当冤大头,不如自开伙仓——后院闲置灶台尚在,找曾师傅商量去。”
我被推作代表,次日下班后磨磨蹭蹭往厨房去。
曾师傅正在收拾灶台,铝锅里剩着半锅白菜汤,汤面凝结的油花如冷透的琥珀。
见我入内,他擦了擦手,腕上的烫伤疤痕在灯光下泛着粉白:“小陈胖子又克扣你们饭钱了?
他那算盘珠子,比走私犯的账本还要精当。”
讨价还价竟耗了两顿饭的工夫。
我盯着墙上贴着的菜单——财政局接待餐标每人四块五,早餐有油条豆浆,午餐必有鱼。
曾师傅将铁勺往沥水架上一磕:“八毛一餐,不能再少
穷,冬天就靠这个续命。”
谢师傅回来那日,我们正围着电饭煲喝白菜汤,他推门进来,肩上扛着半头猪,身后跟着挑竹筐的乡亲:“村里杀猪,非要让我带点回来。”
猪肉在搪瓷盆里码得整齐,他挨个拍我们肩膀:“都瘦了。”
腕上的烫疤泛着粉光,是路上摔了跤护着猪肉蹭的。
黄阿姨次日来上班,往我们嘴里塞炸丸子,烫得直哈气:“老谢跑了三家才凑够半头猪——他说你们四个光棍,过年不能缺了油水。”
腊月廿八,食堂重新开火。
谢师傅将案板搬到院子里,冻得通红的手剁着排骨,骨渣溅在围裙上:“今日吃红烧肉,管够。”
我们支起圆桌,旧台灯罩着红纸当烛台,灯泡将人脸映得通红。
雪花落在黄阿姨煮的甜酒蛋里,很快化了,酒香混着蛋花味,在冷夜里飘得很远。
谢师傅端出最后一道菜,搪瓷盆里五只完整的鸡腿金黄冒油:“招待所用剩的。”
他挠着头,可我们后来看见他躲在厨房啃馒头,蘸着盆底的红烧肉汤汁。
电饭煲在角落静静躺着,锅底的黑印又深了些。
它见过小陈借走的半碗米饭,见过小李分的腊鸭腿,见过老张烤糊的红薯,更见过谢师傅藏在菜里的温情。
当春风吹化冰棱,我们在电饭煲里煮了锅桂花粥——谢师傅种的桂树开了,金黄的花瓣飘在粥面,像撒了把碎金子,却比金子更暖。
这冬天的冷,终究是被灶火、被饭香、被彼此眼里的热乎气给捂化了。
就像谢师傅没说出口的话,都在那半头猪里,在多留的鸡腿里,在每个寒夜里悄悄添的半勺汤里。
第五章 春天的告别式一九九三年的春是蹑着脚来的,梅城的玉兰花开满枝头,白得耀眼,像是谁把冬雪都堆在了树上。
办公楼前贴了红榜,我们四个光棍分了新宿舍,在二楼二〇三室。
老张举着调令在走廊里嚷:“到底不用闻谢师傅的煤烟味了!”
可转身就蹲在宿舍里擦搪瓷盆,把盆底的饭渍擦了又擦——那是三年来每餐与饭勺相斗的印记,倒像是刻在瓷上的年轮。
谢师傅得知消息那日,正在给新栽的桂树浇水。
树苗已长过人肩,枝头缀着星星点点的嫩芽,他说话时没抬头,喷壶的水歪了,淋湿了半截裤脚:“搬新
是我们在煤炉旁分食的烤红薯。”
笔尖划过纸页的声响,像极了当年谢师傅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噼啪间,算出了三十年的情谊。
夜风裹着桂香袭来,新栽的桂树在办公楼前摇曳,枝叶间藏着零星的花苞。
想起谢师傅种的第一棵桂树,如今早已参天,每年秋天,香气都会漫过整个院子,漫过我们留在旧食堂的青春——那些在饭盆里抢肉片的日子,那些用电饭煲熬汤的冬夜,那些被谢师傅藏在菜里的温暖,原来从未走远,它们都沉淀在时光的年轮里,永远芬芳。
(全书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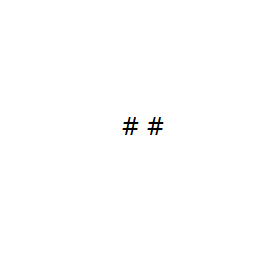
最新评论